首頁>要論>銳評 銳評
張充和:人生實難,唯以風格度過
原標題:張充和 人生實難,唯以風格度過
張充和與傅漢思
【一種懷念】
信手拈來皆故事,張充和追求的卻是“十分冷淡”四字,沒有把生活經營成沙龍女主人的樣子。分明是大時代的親歷者,卻總有一份不動聲色的寧靜。畢竟,人生實難,唯以風格度過。而凡此種種,都不是所謂的才女、貴族、名媛,所能盡訴的吧。
張充和6月17日在美國辭世,享年102歲。消息傳來令人一驚,像是心被撞了一下,生出些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惆悵。
張充和的意義,是要特別一些的。不是因為她詩詞書法昆曲皆精通;也不是因為她與傅漢思的婚姻或是與卞之琳的戀曲,而是那句她以隸書寫就的對聯“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這恬淡而充滿浪漫情懷的兩句話,簡直如這個年代文藝青年的接頭暗號一般,代表著一種最理想的姿態,因而為人所銘記、傳頌、向往。
張充和出身名門,美麗、長壽而有才華,現代人給她扣上“真正的貴族”“最后的才女”的帽子,可是,如此潦草地把她概括為一位空洞的民國閨秀,或不厭其煩地反復強調“合肥四姐妹”和她們各自“傳奇”的婚姻,就像看了場浮華的戲,眾聲喧嘩,卻不免掩蓋了女主角最真實的自我,總歸是有些令人惋惜。
九如巷張家的這位四妹,是最俏皮活潑、不拘一格的小女兒。張充和自小被過繼給叔祖母,請了最好的先生受國學教育,19歲時,她在回憶童年的文章中寫到,小時候坐在屋里讀《孟子見梁惠王》,心里卻掛念著窗外的兩棵梧桐樹,找借口溜出去拾了滿地的梧桐子塞進口袋,叔祖母發現了,倒也不責備,只對她說“生的吃不得,明天我叫他們拾些來炒熟吃”。到了八十年代,她依然不改率真,撰文《三姐夫沈二哥》,往事娓娓道來,落筆還是寫院子里金岳霖寄養的大公雞、來家里聊天的傅斯年、田間勞作的村婦紅棉襖上的黑滾邊。其中一段,寫自己與沈從文逛古董鋪,對方勸她買這個買那個,“我若買去,豈不還是塞在他家中,因為我住的是他的屋子”,讀來不禁莞爾。那個在當年,第二次見這位后來的三姐夫就在心里嘀咕“你膽敢叫我四妹!還早呢!”的張充和,仿佛又躍然紙上,唯不經意間一句“一回首四十多年”,才讓人驚覺,凡此種種,都是前塵往事了。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年輕的時候,張充和粉墨登場唱《刺虎》,有梁實秋和老舍在后臺講相聲給她聽,大學進國文系,胡適點名要她補習算數,就連家中墻上的兩幅畫,也是張大千為她作的仕女圖,說她甩水袖的身段,讓他產生了水仙的聯想。信手拈來皆故事,她追求的卻是“十分冷淡”四字,沒有把生活經營成沙龍女主人的樣子。分明是大時代的親歷者,卻總有一份不動聲色的寧靜。
張充和早早隨丈夫定居美國,生活安穩,沒有像姐姐們那樣經歷政治風云,所以少女時期養成的做派一路保持下來,更為她添了神來之筆。1988年沈從文去世,她為這位三姐夫寫四句挽聯:“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眾人皆稱贊,這四句話的尾綴“從文讓人”,把人名也嵌了進去,她的反應卻是大吃一驚,頻說,“有鬼喲,我可沒有那么想”;她還向余英時調侃自己“玩物喪志”,余英時回敬的卻是:“你即使不玩物,也沒有什么志啊。”——的確,當目睹了許多人世浮沉如煙云過眼,張充和“沒有志”的藝術生活才更讓人稱羨,淡泊而優雅,深情而節制。
一曲微茫度此生,對于所堅持的事業,張充和又有著原則性的堅持。當弟子提醒她,現在的昆曲世界已經變了,她反問:“我已經快一百歲了,難道還要我來迎合你們的昆曲世界嗎?”字字擲地有聲。到底她還是她,走過一個世紀,雅士的風骨仍在。
回頭看,寫下“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這兩句話的時候,張充和已經七十歲了。在這個世俗定義上的“人生漸近尾聲”的年紀,依據扎伊爾德的晚期風格理論,藝術家開始感受到人生時間的急迫性,進而投射在行事或作品中——
晚年的張充和,就這樣展示了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不隨波逐流,也不孤寂,寄情于藝術,又存有知己。如果給張充和的晚期風格定義,她圓融地與世界和解,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個中尺度當然難以拿捏,張充和卻做到了,更難的是恪守了一生。
然而需要承認的是,張充和的去世,的確在現實層面上,為九如巷張家的民國往事畫上句點。另一重意義上,對大部分的我們而言,大約并不能活到張充和那樣102歲的年紀,可是當重逢她的故事和經歷,就像是親歷了那個我們大約走不到的境界,去學習她安身立命的智能,感知她盛名之下的鮮明風格,已經是一種幸運了。
畢竟,人生實難,唯以風格度過。而凡此種種,都不是所謂的才女、貴族、名媛,所能盡訴的吧。
□李青(香港媒體人)
編輯:玄燕鳳
關鍵詞:張充和 去世





 英國鳴禮炮慶賀小王子誕生
英國鳴禮炮慶賀小王子誕生 史上首位虛擬球童誕生 患病小球迷實現夢想
史上首位虛擬球童誕生 患病小球迷實現夢想 土耳其5.1級地震已致39人受傷
土耳其5.1級地震已致39人受傷 3名中國游客在埃及北部車禍中遇難
3名中國游客在埃及北部車禍中遇難 雅典市出任“2018年世界圖書之都”
雅典市出任“2018年世界圖書之都” 馬克龍展開訪美行程
馬克龍展開訪美行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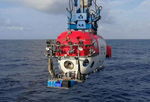 我國首次深海考古調查發現第一個文物標本
我國首次深海考古調查發現第一個文物標本 多倫多市政廣場降半旗悼念汽車撞人事件遇難者
多倫多市政廣場降半旗悼念汽車撞人事件遇難者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