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春秋>聚焦
偽證《蘇聯陰謀文證匯編》的由來

2011年初,李大釗紀念館的尋檔人員在荷蘭國家檔案館發現了一批拍攝于20世紀20年代反映李大釗及其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革命活動的照片,經翻拍后帶回國。其中有一張李大釗同志就義前拍下的全身照,其清晰度之高為國內未見。照片中的李大釗身穿一襲棉袍,雙目直視鏡頭、神色從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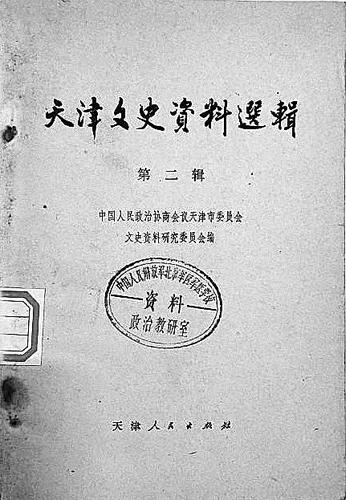
▲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控制的安國軍政府搜查蘇聯大使館,并逮捕了共產黨人李大釗。4月28日,軍政府在看守所里將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秘密殺害,輿論一片嘩然。
為了搪塞輿論,張作霖出版了《蘇聯陰謀文證匯編》,拋出一批蘇聯政府在中國搞“赤化”并組織政變的證據。此書中的材料后來廣泛被傳播引用,給李大釗的名譽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直到51年后,天津市文史資料選輯發表的一篇文史資料,才把歷史的真相揭露出來。
李大釗在蘇聯使館內被捕
1926年4月,張作霖入主北京,自任陸海軍大元帥,并成立了安國軍政府,力主“討赤”,他的部下李景林甚至公然宣稱“不問匪不匪,只問赤不赤”。
1926年4月24日,安國軍政府以“宣傳赤化,毒害社會,貽誤青年”的罪名,殺害了《京報》社長邵飄萍。8月6日,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下令逮捕《世界日報》的成舍我、《民主晚報》的成濟安。
此時,李大釗作為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中國國民黨北方執行部負責人,是馮玉祥國民軍與國共兩黨的重要聯絡人,自然成為“討赤”的重要目標。1926年9月中共中央給北方區委來信,要求李大釗等去武漢創建武漢區委;也有人勸他到天津去避避風頭,但李大釗堅持留在北京,并決定帶領國共兩黨北方機關及全家遷入蘇聯駐華大使館繼續工作。
根據《辛丑條約》,使館區享有治外法權,中國軍警不準入內,有一定的安全性,此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曾在使館區避過難。
李大釗等人進入蘇聯大使館的行蹤很快被京師警察廳偵知,張作霖便以“俄國人正在濫用使館區的庇護,組織叛亂”為由,派出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長吳晉為特使,與西方各國駐華公使進行接洽,請求準許軍警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進行搜查。
外交使團首席公使歐登科于1927年4月4日召開秘密會議,以蘇聯已經退出《辛丑條約》為理由,不再享有領事保護權利,于是各國公使同意了安國軍政府的請求。
1927年4月6日是清明節。上午11時,150多名警察、100多名憲兵全副武裝,從警察廳出發分路直奔東交民巷,包圍并控制了蘇聯大使館。此前已有數十名便衣警察在使館周圍監視。
當時正在蘇聯使館內工作的李大釗等人在完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遭到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李大釗的妻子共產黨員、國民黨員趙紉蘭及其子女,以及蘇聯使館工作人員60余人;抄走文件共463個卷宗,3000多份文件。
“李無確供”,從容就義
李大釗被捕后,一場社會各界的大營救活動開始了。蘇聯政府也對奉系的張作霖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
4月9日,政治討論委員會開會,到會40余名委員認為:“此次東交民巷事件,較為重大,各國觀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僅由軍法裁判,其結果將貽法權委員會以領事裁判權不宜交還之重大口實,實于國家前途貽害甚大。”決定推舉梁士詒、楊度為代表,并邀羅文干一起往見張作霖。
楊度于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國民黨,后來他還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時還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李大釗。因此李大釗被捕后,他斷然以4500大洋低價賣掉了自己的住所“悅廬”公館,全力營救李大釗出獄。在楊度的奔走呼號下,很多名流、進步人士參與了營救李大釗。
章士釗則直接找到安國軍總參議楊宇霆,請他轉告張作霖:“切不可為一時意氣殺戮國士。”曾在北洋法政學堂任教的范熙壬,與李大釗亦師亦友,得知李大釗被捕的消息,連續兩次探訪安國軍總參議楊宇霆未果。1927年4月9日夜,給楊宇霆寫了《致楊鄰葛督軍書》,勸其“消弭內爭,協力對外”,不要“同胞相殘”。
李大釗同鄉摯友白眉初聞訊后,悲憤地大聲疾呼:“大釗是講社會學的,不講主義講什么?難道講主義有罪?難道只興這班強盜講殺人主義、賣國主義?”遂以北京師范大學史地部主任名義,找該校董事長,并聯絡李書華等同鄉及在京教育界名流,積極進行營救活動。
4月10日下午,北京國立九校校長在法大三院開會,議決自10日起,由各校分途營救李大釗一案被捕人員。11日,北大校長余文燦、北師大校長張貽惠訪張學良,適因公外出,由秘書代見,提出:李大釗系屬文人,請交法庭依法審問;李大釗之妻女,請即釋放等條。
樂亭同鄉李時、白眉初、武學易、李采巖等300多人,聯名上書陳情,要求張作霖放過李大釗,釋放其妻子兒女。
當時國內各報都有消息發布,如《申報》《晨報》《北京日報》《民國日報》《大公報》《順天時報》《東方時報》《北京益世報》《北洋畫報》等,《世界日報》更是逐日跟蹤報道。
警察廳一方面對外界宣稱“李大釗口供頗多”,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李無確供”。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4月23日,由于張作霖對此“黨案”不敢進行公審,便決定派參議何豐林就任審判長,組成由軍方控制的特別法庭,不顧各界人士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宣判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死刑。28日上午11時,張作霖決定在看守所里使用絞刑對李大釗等20人秘密行刑,下午1點執行。
李大釗臨刑時毫無懼色,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
拋出偽證混淆視聽
當天下午,張作霖為了向各國公使證明殺害李大釗的合法性,邀請“各外使參觀黨案文件,昨日下午偕赴警廳”。而實際上,張作霖始終沒能從李大釗口中得到蘇聯“赤化”中國的證據,也沒能從李大釗口中得到共產黨組織工農暴動的證據。
蘇聯政府也發表聲明稱,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國的使館里都能得到。張作霖竟然在沒有確證的情況下將李大釗等人絞殺,引起社會輿論一片嘩然。
1927年5月以后,張作霖只得一面下令加大文件公布的數量,并專門成立了一個“查獲蘇聯陰謀文件編譯會”,調動政府中所有懂外文的人對這些文件進行編譯,并向社會不斷公布所謂文件“證據”。
“查獲蘇聯陰謀文件編譯會”的主任叫張國忱,1898年出生在遼寧省遼陽市,哈爾濱俄國商業專門學校畢業,俄文非常好。張作霖對他非常信任,稱他為“自己家鄉的孩子”,故將他調到東三省交涉總署交際處工作,后調張家口任外交部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張作霖派人搜查蘇聯大使館后,為了找到共產國際在中國搞“赤化”的“罪證”,急調張國忱到北京任編譯會主任,令其一方面將蘇聯大使館抄來的所有文件翻譯出來,以找到“赤化”鐵證;同時將這些文件編輯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一書廣為散發。
1928年張作霖被炸身亡后,張國忱任張學良秘書,后任東三省交涉總署首席參事兼交際處處長、鎮威上將軍府咨議、東三省交涉總署顧問兼東省特別區教育廳廳長等職。1931年任天津市財政局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中國人民大學俄文教授。
“精誠所至”探真相
1975年,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恢復。當時,急需找一些人從事文史資料征集,于是有人推薦當時正處于生活困頓中的柴壽安前去。
柴壽安是一位很干練的女性,新中國成立前,曾在1947年創刊的天津《新星報》做過記者,文筆很好,思維敏捷,該報在天津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柴壽安是記者出身,對采訪很在行,因而對征集文史資料很有興趣,也很投入。同時,她也是資深民盟成員,工作中她結識了同是民盟成員的天津美術出版社編輯張鸞,而張鸞正是張國忱的女兒。
柴壽安從張鸞口中得知了其父張國忱的經歷,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重要歷史事件的見證人,而且關系相當密切,他一定知道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秘聞”。于是柴壽安請張鸞引見,想登門拜訪這位深居簡出的老者,當時張國忱已年逾80歲。
但當時“左”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很多人,特別那些曾被認為是“有歷史問題”的人,還是心存余悸,不但不想講述過去的事情,更不敢實事求是地講過去歷史曾發生的事情,因此文史資料征集工作很難做。盡管全國政協文史委多次要求要解放思想,積極搶救史料,但在具體工作中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當柴壽安提出請張國忱先生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時,自然遭到謝絕。張國忱說自己眼睛患白內障,寫不了東西了。柴壽安說可以錄音方式來做,而張國忱說自己年事已高,過去的事情已記不清楚了。所以這個史料的征集過程始終進展不順利。
后來,柴壽安多次到家里找張鸞聊天,在交往的過程中,發現張鸞當時因工作很忙,有時顧不上照顧張國忱的生活起居。于是柴壽安主動提出為張鸞分憂,幫張國忱燒水喂藥、洗衣做飯,攙扶他外出曬太陽,甚至在張國忱臥床不起時,還幫他清理屎尿等。
柴壽安的舉動令張國忱非常感動,以至說柴壽安像自己親生女兒一樣。俗話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張國忱終于同意敞開心扉對柴壽安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了。
經過多次細致耐心的采訪,柴壽安最終于1978年10月完成對張國忱的史料征集任務,寫出《張作霖父子當權時對蘇關系和中東路內幕》一文,發表在1979年《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上。
因為這篇史料的重點是寫張作霖父子在中東路問題上的對蘇交涉,故對《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一事著墨不多,但也足以說明問題了。
遲到51年的真相
張國忱在《張作霖父子當權時對蘇關系和中東路內幕》一文中這樣敘述:
(1927年)四月六日,張作霖派出軍警發動了對蘇駐華大使館的搜查,逮捕了李大釗等多人,同時查獲相當多的檔案、書籍,各國文字都有。張作霖命陳興亞迅速到各機關將凡懂外文的人都調來,盡快譯出。陳興亞遂組織了編譯會,正好原駐海參崴總領事兼奉天代表王之相從海參崴回來,陳遂請王為編譯會主任。張作霖知道后,不大滿意地說:“打電報把張國忱找來,叫他星夜兼程來京。”
在搜查后的第三天,我急忙從張家口趕來,到京后立即晉見張作霖,他在斗紙牌 (張作霖素愛斗天津衛的紙牌),看見我,放下紙牌說:“俄國大使館叫我捜查了,東西全在警察廳,他們組織個編譯會,我不信任他們,你去吧,由你當會長。”又說:“文件、檔案什么都有,要造底冊,每天譯出的東西,要油印出來,給我送十份。叫他們給你發個紅車牌,隨時可以進新華門。”
過了十幾天,張作霖又找我說:“這些天翻出來的東西沒多大意思,沒有向國際上宣傳赤化的材料,要注意查找,這樣可以激起國際上的注意。”
我回去后心想,翻了這么多日子,哪有啊?譯員中有外國記者,我找了一個老白俄,是哈爾濱《喇叭報》的記者。我叫他假造一份向國際宣傳赤化的材料,由王之相譯出,給張作霖送去,搜查蘇眹大使館的這一件公案就算告一段落。
據柴壽安自己所寫回憶文章記載,當時張國忱回憶細節說:
我找來一個白俄記者米塔列夫斯基,是哈爾濱《喇叭報》主編,他和我很熟悉,這次也被我約來參加編譯會工作,我要他按要求偽造一份文件,他勉強答應了。總算搞到一臺與搜查出的文件所用同型號的打字機,俄國造的紙有的燒焦了,有的用水澆得變樣了,只好用新的,盡量做些假裝。偽造件制成后,由王之相翻譯,王在俄文原件上寫了“極要文件”四個字,譯好后,送交張作霖。從此,好幾天,張沒再找我。
天津市政協文史委的同志考慮到當時《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尚是剛出刊的“內部發行”書刊,不會有大問題,因此就發表了。
“鐵證”成偽證
《張作霖父子當權時對蘇關系和中東路內幕》一文發表后,引起北京市社科院歷史所習五一的注意。當時,她正借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寫作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華民國史》的第二編第五卷。她看到了“內部發行”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注意到上面刊登的這篇《張作霖父子當權時對蘇關系和中東路內幕》一文,對其中的這些細節產生興趣,并手持近代史所的介紹信,專門到天津訪問張國忱,并請他確認《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中偽造的材料。
天津市政協文史委的柴壽安熱情地接待了她。在柴壽安的引薦下,張國忱對這套書的來龍去脈做了較細致的介紹,并一一指認了書中偽造、不實之處,之后,他還在指明之處簽名畫押,以保證他所講的真實性。張國忱對柴壽安說:“我對偽造的文件記憶猶新,因其對歷史研究會有影響,故特作以上交代和說明,以供歷史研究者參考。”
習五一回京后,結合其他研究資料,寫了《蘇聯“陰謀”文證〈致駐華武官訓令〉辨偽》一文,并在《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發表,文章細致地分析考證并揭露了這個《蘇聯致駐華武官訓令》,這是一份假文件:由外國公使教唆、張作霖授意、張國忱和白俄記者作偽而炮制出籠。
相似的內容,后來又以《張作霖偽造共產國際文件真相》為題,在《民國春秋》1987年第1期再次披露。
張作霖以偽造的文件,來掩蓋他殺害李大釗等20位革命志士的罪行,真相最終大白于天下。《蘇聯陰謀文證匯編》這個曾被日法美英等國認定的“鐵證”,被一篇歷史當事人的文史資料變成了偽證,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本文作者為天津市政協文史委原主任)
編輯:廖昕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