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人物·生活>秀·風采秀·風采
陳彥:為小人物立傳
2016年1月,中國小說學會公布2015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裝臺》入選年度5部長篇小說排行,并位列榜首。
剛剛過去的2015年,對于陳彥而言注定難忘,慣常于戲劇現代戲創作的他,在當年10月出版了長篇小說《裝臺》,這是繼《西京故事》之后其推出的又一部長篇小說。
《西京故事》劇照
2014年10月,陳彥作為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界的優秀代表,參加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總書記說:“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
《裝臺》正是陳彥在參加文藝工作座談會后出版的一部力作。小說一經推出,即刻引起文學界的廣泛關注。評論家白燁說——
“如果說201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西京故事》,標志著戲劇家陳彥向小說家陳彥成功轉型的話,那么,由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長篇新作《裝臺》,就不僅把陳彥提升到當代實力派小說家的前鋒行列,而且突出地顯示了他在文學寫作中長于為小人物描形造影的獨特追求。”
延續著《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被譽為“西京三部曲”)等戲劇作品的創作宏旨,陳彥的小說依然將自己的筆觸對焦于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2015年的最后一天,帶著這本《裝臺》,陳彥接受了記者的專訪,聊小說、談戲劇、論創作、話人生。
“小說是書寫生存的藝術”
寫作《裝臺》,可以說完成了陳彥長久以來的夙愿。
從1990年到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工作至2013年離開,23年,從編劇到團長、從團長到院長,陳彥與戲劇的緣越結越深。“我的一切喂養,都靠的是這塊土壤,尤其是這塊土壤上生長的人。”
到機關工作,陳彥雖然揮別了戲曲研究院,卻揮別不了那些潛藏于心底的人和事。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都成為他寫作的資源寶庫。早在七八年前,寫一部反映“裝臺人”生活的小說的想法就在他心中生成。
隨后數年,幾易其稿,距離的產生反而激發了陳彥的創作熱情,經過沉淀、加工、修改,2015年終成此稿。
《裝臺》描寫了一群常年為專業演出團體搭建舞臺布景和燈光的人。打了20多年交道,對于“裝臺”這樣一群人,陳彥有著天然的親近感,他從這個小行當中琢磨出了大滋味——
“有人說,我總在為小人物立傳,我覺得,一切強勢的東西,還需要你去錦上添花?我的寫作,就盡量去為那些無助的人,舔一舔傷口,找一點溫暖與亮色,尤其是尋找一點奢侈的愛。”
在陳彥看來,裝臺工作雖然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是陌生的,但他們在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重,他們的堅守與掙扎,光榮與夢想,與我們卻沒有根本的不同。“我熟悉他們,甚至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歡樂著他們的歡樂,憂愁著他們的憂愁。”
《長篇小說選刊》2016年第一期全文選載了《裝臺》,卷首語這樣評價——
“關注底層小人物并不難,難的是你了解不了解他們的營生勾當,熟悉不熟悉他們的言語做派,對他們的內心和命運有沒有足夠的體察和思考。陳彥熟悉舞臺,熟悉后臺,他用小說的方式把隱身于帷幕背后的裝臺人推到了前臺,讓讀者隨著刁順子和他的伙伴們的勞苦努力、悲喜哀樂而俯仰感嘆,而有所領悟。”
在《裝臺》中,主人公刁順子和他的一幫弟兄們長年奔走于西京城的各個舞臺,干著最累的活,說著最軟的話,受著難忍的氣,在一個又一個的裝臺現場為生活奔命。雖然生活極盡苛刻,數次讓刁順子在困境中難以突圍,被逼得進退失據,但他從來都是認認真真勞動、踏踏實實工作、本本分分做人,“幫襯著一起裝臺的兄弟,關照著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
評論家李敬澤說——
“很少有一本書會像《裝臺》這樣,我拿起來,竟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了,在那喧鬧的生活里,在那些渾身汗臭的男人和女人身邊,和他們一起過著狼狽不堪的日子,而我竟不想放下不想離開。現代小說常常空曠,而《裝臺》所承接的傳統中,小說里人頭攢動、擁擠熱鬧。《裝臺》的人物,前前后后,至少上百,大大小小,各有眉目聲口。大致上是以刁順子為中心,分成兩邊,一邊是他在裝臺生涯中所交道的五行八作、人來人往,另一邊是他的家庭生活,特別是通過他女兒菊花牽出的城中村的紛繁世相、形形色色。兩邊加在一起,真稱得上是呈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
陳彥說:“小說是書寫生存的藝術,書寫生存的卑微與偉大、激情與困頓”。《裝臺》正是展現了這樣一群在底層掙扎的小人物們困苦而莊嚴的生存故事。
“重新撥亮一種價值”
讀完小說《裝臺》,人們或許會發現,裝臺人也有他們的“生活邏輯”,有他們的價值堅守、責任和擔當。在陳彥眼中,刁順子們持守正道,以誠實勞動安身立命,這就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延續的“恒常價值”,時代的變化并不應讓這些基本的價值失色或者暗淡,陳彥自覺地在藝術作品中不斷撥亮,讓其光華不減。
陳彥筆下的人物起點并不高,但作品中對底層人生活困境的挖掘卻十分充分。從《遲開的玫瑰》中的喬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羅天福和《裝臺》中的刁順子這些人物身上,我們讀出了困境之中他們的成長與突圍。
陳彥的作品總是著力展現這些身處生活底層的普通人的生命價值與尊嚴,讓人們在對其滿懷愛與悲憫的同時,生發由衷的敬意。
講述20世紀50年代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現代戲《大樹西遷》,沒有寫遷校上層的方案之爭與宏大場面,而是將焦點對準一個最普通的青年女教師孟冰茜,用她五十年的生命史,從反對西遷,到完全融入西部生活,并深沉地愛著西部,多側面多角度展示了她苦難一生、奮斗一生、奉獻一生的心路歷程。
在陳彥看來,小人物,普通人,永遠是他書寫的主體。他認為,城市中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值得更多人關注與書寫。一個大城市,少則幾十萬,多則成百萬,甚至數百萬外來務工人員,他們往往出現在這個城市最破爛、最骯臟的地方,清掃馬路、建設高樓、疏通管道,干著最苦最累最臟的活兒,一旦哪里建設得花壇簇擁,一道圍墻便把他們永遠擋在了墻外。是什么東西在支撐著他們在城市的邊緣謀生,支撐著他們在苦難中前行?是什么樣的生命信念讓他們堅持著這種謀生方式,守望著他們的生存與道德底線,且長期與城市相安無事,一切的一切,都值得城里人很好地去回眸、關注、探究,并深刻反思。
陳彥在用一部部戲劇作品、也在用一部部小說作品回答著這些問題。
在評論家吳義勤眼中,陳彥的長篇小說《西京故事》“沒有理念化地將農民工作為簡單歌頌的對象,也沒有將城市簡單塑造為欲望都市,而是站在中立的基點,在人性的視野內,審視兩者的關系,以此凸顯民族精神在壓抑中的延展”。
“《西京故事》延續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開創的思想傳統,直面現實,本著‘為普通人立傳’的主旨,緊緊扣住‘尊嚴’兩個字,努力挖掘并呈現時代之痛與當代人的心靈之痛,全面展現當代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困境,立體而多維地揭示了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史、人性救贖史。”吳義勤說。
陳彥除創作外,還發表了大量文論、評論,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創作要持守恒常價值”——
“我不喜歡在作品中過多地演繹新觀念,而始終在尋找人類生活中的那些恒常價值。人類生活是相通的,都要向善、向好、向美、向前。那些經過歷史檢驗,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對人與人之間適當關系調節起著永恒作用的長效價值,可能是我們每一個時代都需要進行重新闡釋,重新撥亮的價值。”“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需要對一些價值觀進行重新省察、甄別,有許多值得重新撥亮,撥亮之后,這些傳統價值就是時代的,甚至可能成為一個時代的最強音,比如厚德、比如誠信、比如以誠實勞動安身立命等等。”
陳彥說:“聯系到城市中這樣一群數量龐大的農民工,我覺得他們始終堅守著一種東西,那是中華民族甚至人類最為樸素的恒常價值,這些價值讓他們的勞作,讓他們這些小人物的人生充滿了堅韌性、道德感和尊嚴感。”
無論陳彥的戲劇“西京三部曲”,還是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裝臺》,都讓人們看到普通人也能活出生命的尊嚴。普通人正大光明地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勞去坦坦蕩蕩地獲取自己的勞動所得,這樣一種人生也是有尊嚴、有價值的人生,也是我們社會應該大力提倡、關注的人生。
陳彥始終相信,藝術家不僅要有悲憫情懷,還需要認同甚至提升普通人的生命尊嚴。“我們需要走進他們的生活,進入式地去審視他們的生活,不能漠視甚至指斥他們的生存價值。”
“我比較能下笨功夫”
在陳彥看來,到要創作時才去尋找素材、深入生活,這對寫作而言是困難的。創作是對生活深入咀嚼后“化棗為泥”般的自然流淌。
面對如今文化快餐消費的時代,陳彥有著自己的堅持。他的作品在“出籠前總是慎之又慎”,需要靜靜地梳理、思考、沉淀、打磨。他認為,創作一部文藝作品,一定是“內心有話想說”,并且“是別人沒說過的,如果都是別人已經說過的,而且你說的還沒有別人好,沒有別人精彩,那你說這個的必要性就不大。”
陳彥堅信,如果作家對生活沒有感性的、內化為自己生命里的一種感情、認知,那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比較“隔澀”。
為了寫出個性飽滿的人物形象,陳彥始終將自己與所描寫的人群置于同一位階,無須仰視亦無須俯視,而是平等地走向他們的生活、認同他們的生活、感受他們的生活。評論家雷達說——
“《裝臺》是在人們,也包括作者自己沒有事先預謀和明確期待的情況下積少成多寫成的。《裝臺》與時尚的小說觀念沒有多少關系。作者只是寫他的觀察已久,爛熟于胸的人物以及環繞他們的世界,沉浸其中,才造就了這部人物活靈活現,世情斑斕多姿的現實主義力作。”
陳彥常常琢磨“裝臺”這個特殊的群體。他發現,“他們大多數是從鄉下來的農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這些城里人就是他們的‘主心骨’,當然,也有的成為他們的‘南霸天’。”
在寫作之前,陳彥還特地找來幾位比較熟悉的裝臺工作者,進行了長談,做了好多筆記。正是平時這種細致的觀察,和創作前的長期準備,“黏合了好多裝臺人的形象”,才有了刁順子這樣真實豐滿、充滿個性的人物。
在陳彥筆下,主人公們往往面對著內心的困境、矛盾與兩難選擇,當兩難選擇被完整呈現、人生困境被真實再現、心靈世界被充分打開后,主人公們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做出了持守正道的人生抉擇,這樣的人物形象是在充分的張力中呈現人物內心的糾結、矛盾與反復,而在這樣的鋪陳后,人物最后的選擇就是一種水到渠成。
評論家孟繁華說——
“好小說應該是可遇不可求,這與批評和呼喚可能沒有太多關系。我們不知道將在哪里與它遭逢相遇,一旦遭逢內心便有‘喜大普奔’的巨大沖動。陳彥的長篇小說《裝臺》就是這樣的小說,這出人間大戲帶著人間煙火突如其來,亦如颶風席卷。”
從《遲開的玫瑰》中的喬雪梅到《大樹西遷》中的孟冰茜,從《西京故事》中的羅天福再到《裝臺》中的刁順子,人們感到陳彥筆下的這些人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身邊。有評論家認為,這些主人公在陷入重大人生困境之中時的選擇與堅守,少了一分“矯揉造作”,多了一分“生活使然”。這也最終使這些人物能夠站住并且為讀者和觀眾所認可。
“這就是我們身邊真真切切的一個人,而人物的心路歷程也會走得相對比較完整。”陳彥說。
寫《西京故事》時,陳彥當時所在的陜西省戲曲研究院的門口,每天晚上都有十幾個農民工在單位的屋檐下打地鋪住著。為了對他們的生活有更深入地理解,他先后到西安的東、西八里村,訪問過數十戶人家。這個當地居民僅3000多口的城中村,竟然居住著10余萬農民工和附近上學的大學生。
而走進西安木塔寨,這個原本1500余人的村子,卻密集充塞著50000多農民工。陳彥在小說《西京故事》的后記中寫道:“只有深入進去,觸摸到了那一家一戶、一攤一店地形復雜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實感受到這個特殊群落的人性溫度與生命冷暖。”
寫《大樹西遷》時,陳彥在西安交通大學深入生活4個多月,隨后到上海交通大學住了35天,前后找了100多位教授、學校管理層和學生進行交談。陳彥說:“創作之前的做功課比創作本身下的功夫要大。《西京故事》舞臺劇只有兩個多小時,但是我后來寫了50多萬字的同名長篇小說,我多少年跟蹤農民工生活,舞臺劇只能表現很小的一塊,大量的生活素材,尤其是對城鄉二元結構當中所出現的社會矛盾進行的思考無法運用,最后必須用長篇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
看過陳彥戲劇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觸,合轍押韻的唱詞、扣人心弦的獨白、婉轉高亢的唱腔讓人聽得如癡如醉。從那些堪稱經典的唱詞中,我們讀出了現代人的情困糾結,更讀出了富有傳統意味的雋永深沉——
“我喜歡寫舞臺劇,是因為我喜歡古典詩詞,喜歡唐詩、宋詞、元散曲。中華傳統文化真的是奧妙無窮,有些作者將句子錘煉得那么精彩、那么情景交融、那么‘一石三鳥’,尤其是元曲,竟然那么生活、生動,那么有趣,雅能雅到不可‘狎玩焉’,俗能俗到像隔壁他大舅與他二舅聊天對話,真是一種太神太妙的藝術境界。”
陳彥說他的唱詞寫作,也與早年為數十部影視作品創作近百首主題歌詞與插曲詞有關,歌詞提煉與戲曲唱詞創作有異曲同工之妙,都需壓榨,都需凝結,都需“以少勝多”。大量的歌詞創作,還讓他在戲劇、文學創作之外,收獲過《陳彥詞作選》的結集出版。
陳彥始終信奉這樣的觀點:“寫歷史劇,需要認真研究現實,而寫現實題材、寫當下社會,則需要更多地關注歷史,只有對歷史有比較深入的學習和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當下和未來,如果我們割裂了對歷史的學習和認知,我們對當下的把握很可能是浮泛的、短視的。”
陳彥學習歷史、學習傳統,那是下了真功夫的。他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擔任院長10年,有晨跑的習慣,每天早上一個小時。別人都以為他在鍛煉身體,其實,陳彥在晨跑中完成了一個龐大的學習計劃——背誦元典。
從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逍遙游》《齊物論》《秋水》,到《大學》《中庸》,再到17000萬多字的《論語》,還有35000萬多字的《孟子》,陳彥都是在日復一日的晨跑中完成背誦的。
當年,陳彥創作電影劇本《司馬遷》,他認真地將《史記》通讀了四遍,而且閱讀的是四種不同的評注版本。每讀一遍,他描紅批注都是密密麻麻——
“通讀完了之后還是找不到人物形象,后來我將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背了下來,隨后在構思劇本的時候,躺在床上一邊背著《報任安書》,一邊在頭腦中復活司馬遷的人物形象,他的為人、做派、性格、性情、說話的語言表達方式逐漸清晰。”
劇本創作如此,對于書法學習,陳彥也表現出同樣的執著。二十年前,陳彥有了學習書法的念頭,別人告訴他要多多臨帖,陳彥就先用三年時間將《圣教序》臨了100遍。
陳彥說,如果自己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那就是“比較能下笨功夫,認真做好每一件該做的事,無論創作還是工作,都當如此”。
“繼續保持藝術的敏感”
1979年,16歲的陳彥學習改編了舞臺劇《范進中舉》,這算得上是他在戲劇創作上的牛刀小試。1980年,他創作了第一篇小說《爆炸》,寫的是政府改河工程給小人物帶來的生存危機,發表在內刊《陜西工人文藝》上。
1981年,陳彥開始在鎮安縣劇團學習編劇。在那幾年中,他寫了6部大戲,有現代戲,也有歷史劇,形式上有話劇,有山歌劇,也有地方花鼓戲。
而在陳彥22歲那年,甚至有幾個不同的演出團體,將他創作的《沉重的生活進行曲》《愛情金錢變奏曲》《丑家的頭等大事》等多部劇作同時搬上舞臺。
跨進藝術之門的陳彥在隨后的創作道路上不斷收獲著被汗水浸潤的果實。舞臺劇《九巖風》《留下真情》等劇紛紛進入國家級平臺調演展演。這期間,他還創作了30集長篇電視劇《大樹小樹》,不僅在央視一套播出,而且還獲得了“飛天獎”和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更是讓陳彥蜚聲戲劇界,所獲榮譽可謂將這一領域的大獎“一網打盡”。
《遲開的玫瑰》從創作到現在已經快20年了,在陜西和全國二十多個省市演出近千場,至今依然常演不衰,并有多家劇團多個劇種移植上演。《大樹西遷》也已保持了14年的持續演出生命力。
《西京故事》搬上舞臺僅4年多,但演出已近500場,不僅在大西北的“秦腔窩子”里斬獲盛譽,而且在遠離秦腔本土后,先后在廣東、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吉林、黑龍江、福建、海南、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省市的數十所高校巡演,贏得老師和學生的普遍贊譽。
各種評價體系中相對集中的關鍵詞是:“真實”“深刻”“感人”“接地氣”“正價值”“正能量”。當說到“三部曲”的成功時,陳彥屢屢談到——
“陜西省戲曲研究院是黨中央在延安時期成立的一個戲曲文藝團體,七十多年的歷史,已經讓這個院聚集起了一大批頂尖藝術人才,他們敬畏藝術,敬畏規律,敬畏創造,所謂‘西京三部曲’,是這個團隊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只是一個受益匪淺的編劇。”
收獲榮譽的同時,這些作品也在收獲著歷經時間檢驗的贊美。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的夸獎;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陳彥看來,“用傳統形式來表現現代生活內容是可行的,是沒有障礙的,關鍵是看你與時代血脈接通了沒有。一切藝術都是可以穿越時空地域限制的,關鍵是看你走進他心靈了沒有,走得有多深,其深度決定溫度”。
陳彥從來不以成功者自居,但是,在創作道路上的他,如一位斗士,不斷地嘗試著不同創作式樣的可能性。
散文集《必須抵達》《邊走邊看》《堅挺的表達》讓人們意識到,戲劇家陳彥同樣也是生活的思考者、社會的觀察家與語言的設計師。每一本散文隨筆集無不文香盈盈。
繼《西京故事》《裝臺》兩部小說后,陳彥即將進入第三部長篇小說《旦角》的創作,寫站在舞臺中心的“主角兒”的生活。陳彥說:“他們既是舞臺上的主角,有時也是社會的主角。這部小說將從舞臺輻射到相對廣闊的社會生活。我對他們的生活很熟悉,以前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的時候不好寫,沒有與他們拉開審美距離,我調離戲曲研究院到機關工作后,這些人物的形象常常撲面而來。”
當被問及是否已將創作重心轉向小說時,陳彥說——
“小說是一種個體閱讀,而戲劇欣賞則集合了幾百、上千甚至數千不同背景、身份、年齡的人們,有時一場好戲甚至達到萬人同看。戲劇這種群體觀看的作品樣式與小說這種個體閱讀的作品創作,在很多處理上是不盡相同的。無論寫舞臺劇還是小說,都是為了讓人觀賞、閱讀,但是我們必須為受眾思考一些問題,要認識到觀看者、閱讀者的不同感受。一群人集體看與一個人個體看,有時感受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什么東西你覺得是合適的,觸動了你的創作神經,你有表達的欲望,并且你認為用這種方式表達最合適,就用這種方式表達好了。”
訪談到最后,記者問陳彥平常對自己的時間都怎么安排,他畢竟還有機關工作纏身——
“再忙的人,都有學習思考的時間。我在工作上沒敢馬虎過,并且機關工作還經常占用節假日和晚上時間,因為我負責的是文藝工作這一塊,好在與我的專業有關,也算是駕輕就熟吧。一個人只要有心,就會有很多時間。”
陳彥將寫作視為“肉身給心靈的思想匯報,是自我對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的定期定時的盤整回望,是心靈的自然需求”。
陳彥說:“我現在每年的閱讀量是60~80本書,有空便開卷,尤其是出差路途,讓書籍填充得十分愉快,作家需要開闊的思想和生活視域。我認為無論是一個創作者,還是一個機關公務員,都需要不斷地閱讀和思考,閱讀和思考可以讓你的創作更好,也能讓你把工作做得更好。”
結束訪談時,陳彥正要出差,記者看見他把厚厚兩本書塞進拉桿箱,都是哲學著作。他說:“閱讀是很快樂的事情。尤其是出差,你想,一路跟比你高出不知多少倍的高人對話,豈不快哉。”
陳彥
陳彥,1963年生,陜西省鎮安縣人,一級編劇,中共十七、十八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創作《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等戲劇作品數十部,三次獲“曹禺戲劇文學獎”“文華編劇獎”,三度入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創作電視劇《大樹小樹》獲電視劇“飛天獎”,多次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首屆“中華藝文獎”獲得者。出版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裝臺》,散文隨筆集《必須抵達》《邊走邊看》《堅挺的表達》,以及《陳彥劇作選》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文化部優秀專家,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為資料圖片)
編輯:邢賀揚
關鍵詞:陳彥 《西京故事》 戲劇 長篇小說 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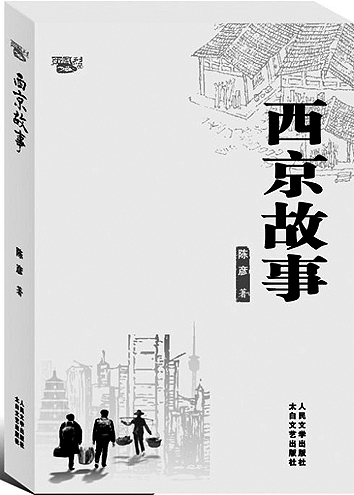



 貴陽機場冬日為客機除冰 保證飛行安全
貴陽機場冬日為客機除冰 保證飛行安全 保加利亞古城歡慶“中國年”
保加利亞古城歡慶“中國年” 河北塞罕壩出現日暈景觀
河北塞罕壩出現日暈景觀 尼尼斯托高票連任芬蘭總統
尼尼斯托高票連任芬蘭總統 第30屆非盟首腦會議在埃塞俄比亞開幕
第30屆非盟首腦會議在埃塞俄比亞開幕 保加利亞舉辦國際面具節
保加利亞舉辦國際面具節 敘政府代表表示反對由美國等五國提出的和解方案
敘政府代表表示反對由美國等五國提出的和解方案 洪都拉斯首位連任總統宣誓就職
洪都拉斯首位連任總統宣誓就職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